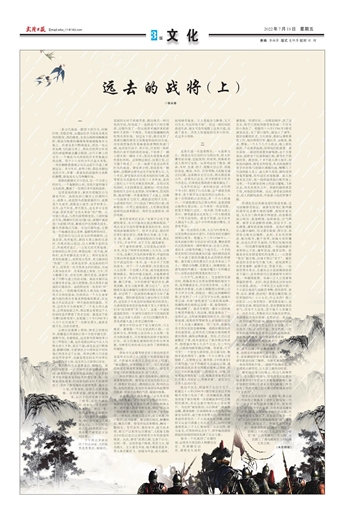◇杨永雄
一
一条古代商道一眼望不到尽头,时断时续,若隐若现,从邈远的岁月深处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的脚底,在崇山峻岭间蜿蜒曲折,像战马散落的缰绳弯弯绕绕拖曳在大地上。沿着这条川黔商道走,到达一处山形如腾飞的骏马背上,两块历经两百年风雨的神道碑就会矗立眼前,注目石碑上的文字,一个被血与火淬炼的历史形象就必然出现。那个十六岁的少年已高大英俊,一双赤脚踏着漫漫尘灰从这泥石古道上渐渐远去。多少年后,星移斗转,那位赤脚出走的少年,穿着一袭黄色的战袍和火焰般的簪缨,骑着高头大马挥鞭归来。
我感到震撼又不可思议,在一个马背上的村庄,一个偏僻的山村,寻找古道和铺子文化的我,遭遇了一位两百多年前的战将。
这里是他的故乡,重庆市武隆区白马镇东升村。战将在自己履历上自谓四川人、成都人,或是因为武隆原属四川,成都是个大地方,武隆是小地方,东升村更小。东升,这个村名,并不悠久,也无多少文化内涵,很显然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山村很小很远,几经行政管辖变化,三国时属汉平县,隋唐时归武龙(隆)县,清朝时属涪邑(今涪陵)西里,解放后归长坝镇茶园乡,撤乡并镇属白马镇。无论归属何地,它都是一个躲藏在深山老林、偏僻荒野的村庄。
苍茫的白马山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山高谷深,地形起伏,源自大娄山脉的长途河、石梁河抚山而过,注入奔腾不息的乌江,形成两河连江、一山突兀的天然地理。在倾斜的山脊之间,难得出现一处平地,板桥村、东升村静伏在马背上。两村东面光秃秃的悬崖上,刻有宽大笃实,笔力雄浑的“豹崖”二字。说来也奇异,在这高高的马背上,居然有一处天然泉水汨汨涌出,当地人称为凉水井。往来商道上客商、力夫、行人歇脚于此,历史交织,朝代更迭,逐渐形成了川黔大道上的凉水铺。离凉水铺不远处建有青玄庙,虽几经毁废,但大型条石砌成的石墙尚存。庙的附近有一处形似“凹”的地方,一些附庸风雅的人称为卧马槽。我不太相信宿命,但我承认一个人生命来路与他的故乡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在血脉之外应该还有一种天地化育的基因。不然,近些年不少游客到了一个名人伟人故里,去拜谒祖屋之外,都还要去看看这个人的祖坟是否葬着了风水宝地。就是这个卧马槽(俗称弯里),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八月十五日迎来了一位新生婴儿,他原名曾月先,后改名曾受。
从曾氏祖墓碑上得知,曾受之祖曾启仲,原籍是江西省临江府十字街市铺宅居,康熙年间,为避祸乱,远迁贵州思南府务川县三甲暂住三载,也许是曾启仲这个汉人与黔北苗人不和,语言不通;或是走过川黔商道,歇脚间隙,无意摆谈之中得知东升村皆是江西老乡迁于此地。再次由黔入川迁徙涪邑西里首甲,也就是现在的东升村青杠堡。买冉家土地,远迁风尘之旅得以安定。
春天的阳光总是柔柔的、暖暖的。葱绿的田野里,一片片树叶在徐徐微风中摆动,被春阳照着显得亮晶晶的。在这样的季节里我驱车来到东升村青杠堡,在一位貌显恬淡温柔、时尚俊俏的女村干热情帮助下,见到了曾受隔房后裔曾宪甫,他年近八旬,中等身材,显得几分清秀儒雅。谈到其家族,曾宪甫侃侃道来,从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到了曾受,说到我疑惑时,他拿出一本手抄的族谱作证。接过一看,我知道有些是牵强附会,但许多事都不能探究,稍一探究就让人疑窦丛生。几个小时交流之后,他带我去一公里外看了曾受祖父母的坟墓。
下午两点多钟返回了村活动室,太阳依然是柔柔的、暖暖的。美丽的女村干部微笑着,露出珠贝一样闪亮的牙齿,给我泡了一盒舒适可口的方便面,还额外加了一些从地里采摘回来的新鲜叶子菜和一个鸡蛋。早就饥肠辘辘的我吃得舌香肚饱。别过女干部,最后走到了我感兴趣的曾受父母墓地和他的出生地。没有我想象的有着凝重而肃穆的朱漆门阙,也没有旧房子、青石坎,只见到一排新修的白面平顶砖混的房屋,下面停了一辆小轿车和一辆皮卡车;更没有我想象的那些苍松古柏。这里物过境迁,沧桑巨变,已不属于曾受了,一点一滴看不见过去所有时光的痕迹。曾宪甫介绍,原房前有一颗棕树,这颗树从曾受出生开始发芽生长,几十年后,曾受每次回乡成为他的拴马树,孤零零在风雨雷电中长到三十多米高,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被狂风吹倒。在那日风初刮时,人们仿佛看见,棕树如一把长剑在昏暗的天空中东杀西拼,呼呼嘶鸣,罡风阵阵,继而咔嚓一声重重倒在了大地上,仿佛一位战将无力回天,满脸悲切仰天长叹。去清理砍伐时,刀口流出了鲜红的汁液,将树根处一片黑土洇染殷红,人们都说那是战将的血液和眼泪。我听完也感惊奇,将信将疑。
著名作家陈启文说:“如果不立足于坚硬的现实,也不可能真正抵达精神现场。”我认为文学创作要尊重真实的历史,坊间传闻会被微风吹干。经多方求证,曾启仲在青杠堡定居后,得配贺氏为妻,生下奇、文、俊、荣、敏。三房曾俊配冉氏为妻,得长子月礼,不幸早卒,次子月先,就是曾受。
对于童年的曾受,父母是他必读的一本书,学会了呀呀学语和树上九只鸟,打掉一只鸟,还剩几只鸟的简单数学;早逝的祖父曾启仲是他最早的启蒙老师,也是他一生中读过的另一本书,是一本合不了页面的读本。对于一个人的领悟,往往要从他人生的第一个启蒙人开始,成为他最初的精神源头。曾启仲能文能武,文能教曾受识文认字、吟诗作文;武能教曾受拳打脚踢、舞刀弄棒。少年的曾受“粗识诗书,酷爱武略,及长力能举鼎,臂力过人”。这些描述虽是后来编写出版的《武隆文化志》记载,却证明了一位战将的基础功力有了基本铺垫。那时曾受的祖父曾启仲万万没想到,这位孙子未来会给他增添死后的荣光:大清帝国皇帝诰封他和妻子及儿子曾俊夫妇为“武功将军”及“夫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生留给后裔们不可忽视的荣耀,也让当地人找到一点可以炫耀的资本,更是武隆大地上有史记载的唯一。
曾受少年时从学于祖父曾启仲,习文练武。清朝是一个以文驭武的王朝,一旦国难当头,那些纸上谈兵的士大夫便一变而为软弱懦夫,只有刚强的战将才能领兵打仗。祖父的避乱避祸的经历和言传身教,为曾受后来的戎马生涯作了潜移默化的铺垫。
我如今无法稽考曾受祖父曾启仲是否也是弃文从武之人,但至少知道他能文能武,不然嘉庆皇帝怎么会在诰封上写道:“威宣阃外,家传韬略之书”。可以看出曾启仲是位熟读军事韬略之书的人,曾受受其祖父的影响爱读兵书、好习武艺。
弗洛伊德认为,童年是性格和心理形成最重要的时期。曾受是实实在在的大山之子,那粗犷的山石,凛冽的山风,坎坷的山路,危险的悬崖,在他的生命深处构起剽悍而坚毅、顽强而血勇的气质,倔强的性格。
孟子说,一个成大事者,“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正当曾受习文练武用功时,他的祖父母及母亲在饥病交加中相继去世。离开亲人的督导和关爱,使他“常出没于赌场集市,放荡不羁”。没几年,“家资耗尽,一贫如洗,贫病交迫之中,其父病逝,停尸数日,无力安葬。舅父冉氏闻讯,解囊相助,嘱其归葬。曾受持钱却奔赌场,瞬间一输而光。无可奈何,潜回家中,趁天色未明,将父尸以稻草包而葬地”。《武隆文物志》中的记述足以说明曾受少年的放荡和叛逆。从此,曾受“流落江湖,乞食于白马、长坝一带。长坝有富户杨某,见其力大,留为佣人。主人善交多客,每天剩饭菜甚多,常入夜不翼其飞。初疑为外盗,派人窥视,始知曾受偷食。主人爱他卖力勤事,又不讨分文,对此佯装不知”。经过一段时间的浪迹生涯,他无可奈何地踏上这条古道,远离了故乡。没有人知道他经历多少坎坷,走过多少弯路。
二
这条古道一头连着黔北,一头连着乌江。商道从乌江边的白马场出发,经大斜槽至凉水铺,过赵家坝、何家坝,到鲁班岩进入贵州万宝场。从贵州运出了粮食、桐油、木材、生漆、棓子、猪鬃大宗山货,再换回食盐、煤油、布匹、百货等物。《武隆交通志》记载,这条路全长百公里,两头都连着山外。连着乌江这头,年少的曾受不知多少次走过,后来他走得离故乡越来越远了。
从东升村穿过一条斜坡古道,步行两个多小时,便到了白马古镇,这个镇原名铁佛寺,是个很早设立盐官的江边码头。一条十分明净的江水岸边,有一个小小的渡口,一只渡船摆过乌江南北两岸,连着武陵山脉和大娄山脉。江中常有一些歪屁股、舵笼子等船只过往,一些木排、竹排也混入其中。曾受就是从这里坐上一只小船或是一个筏子出发的。谁也不知道,也不会有人操这个心思,这个少年终将渡向哪里,又会走多远。
每一位出世的人物,又总与时势有关,历史仿佛在宿命中进行,不到历史的关键时刻难以现身。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一场来自廓尔喀(今尼泊尔)的突袭,裹挟着黑沉沉的西南风一路呼啸而来,在突入济咙、聂拉木、宗喀等西藏三个地方后,一个手持库克利弯刀的民族愈加兴奋,他们感到进攻一个大清王朝的西藏是如此的轻松和舒畅。廓尔喀王国的素尔巴尔达布率兵三千人,一路跃马扬鞭,长驱直入,纵横劫掠,大清帝国的西藏又一座城市噶尔(今西藏定日),出现在他们明晃晃的弯刀之下。
六月天气,凉爽宜人。当急报传至清宫时,乾隆皇帝正在那金碧辉煌的寝宫午休,虽然睡意全无,只在闭目养神。心里正得意洋洋想着,大清王朝版图从明朝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到他这一朝已达到巅峰时期,扩张到了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地域非常辽阔,形成“康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他睡眼惺忪地接过急报一看,脑袋嗡的一声就清醒了。他没有想到一撮尔小国的廓尔喀居然敢侵入我边境,便迅速做出了一连串反应,立即派理藩院侍郎巴忠、四川提督成德、成都将军鄂辉等人率领满汉官兵三千人火速入藏御敌。另一方面,乾隆皇帝又传旨安抚达赖喇嘛。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意图是,必须用武力使廓尔喀侵略军震伏惕怵,确保边隅静谧。然而,巴忠以迁就敷衍了事,轻率地答应了廓尔喀议和条件,赔偿廓尔喀人九百个元宝,分三年付清,以换取侵略军撤出西藏。你看看,可不可笑?一个堂堂大清帝国,在兵强马壮、粮饷丰富的情况下,竟被一个小小弹丸之国侵略了,还要赔元宝、赔笑脸。《中国通史》后来写道:“由于西藏距北京遥远辽隔,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对西藏局势难以周察,所以巴忠向乾隆谎报‘已将聂拉木、宗喀、济咙等地次第收复’之后,乾隆皇帝竟然以为巴忠等人为国宣力,劳绩卓著”。着实为巴忠等人论功行赏。
纸包不住火,阴谋终于大白于天下。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方面以不纳贿币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乾隆皇帝鉴于廓尔喀第一次侵藏战争中巴忠贿和的教训,其反击廓尔喀的决心坚如磐石。为达到“痛加惩创,示以炯戒”,他高瞻远瞩,潜谋独断,任命刚收复台湾的爱将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大臣,带领骁勇善战的索伦兵二千人迅速赶赴西藏,清政府又从金川调遣土屯兵五千人,从四川调遣绿营兵三千人汇集前线。众兵压阵,铁马金戈,只等统帅反击令下,那早被战前风鼓起的战袍顷刻间充满了反击力量。
每当一个民族到了关键时刻,必将有不世出的人物横空出世。所谓横空出世,需要长久地积蓄势能。所谓历史,一切都是顺序,到了这关头,似乎已经轮到曾受来扮演一个历史的小角色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曾受离家远走,为了混口饭吃,就加入了清军。据说他勤恳机灵,力大敦厚,最初从事炊事班工作,每次移营行军,搬灶具、运粮食、挑水、劈柴,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晚上常给副将、千总煮菜温酒,深得他们的喜爱。某日深夜,一副将到来要加餐喝酒,由于天寒地冰,副将坐于灶前取暖打盹,曾受忙于煎油炒菜。疏忽间,十多个敌人潜入帐中,伺机赴向副将,曾受忽然惊觉,机灵的他顺手用手中的铁勺将锅中沸腾的油,唰唰几下尽浇到敌人身上,敌人猝不及防,瞬间受烫得鬼哭狼嚎,纷纷退后伏地躲避。敌人惊魂未定之际,他一抱将副将抱出账外放上马背,一手扯断拴在树上的战马缰绳,飞奔远去,消失在夜色之中。得救的副将感恩于他,对他倍加青睐。从此,曾受走出炊伙房,投入到前线战场,开始展示他的军事才能。
所谓乱世出英雄或是时势造英雄,这句话被曾受验证。福康安统领汇集西藏的清军反击廓尔喀的侵略,很快收复失地,又兵分三路向廓尔喀挺进,沿途都是高山峡谷,悬崖峭壁,海拔极高,空气稀薄。廓军又沿途断桥设障,层层卡子,处处碉堡,清军前进极为困难。在攻打喝勒拉山颠木城时,侍卫墨尔根保、图尔岱,参将张占魁先后牺牲。此时,又有风雪肆虐,帐内帐外,整个世界,皆被大雪所覆盖,在这白茫茫天地间,行军打仗相当艰难。一时间清军情绪低落,一些摇唇鼓舌者想停止不前,撤军罢战,谋求议和。乾隆皇帝坐在舒适宽松的龙椅上,一心想要“惩处”廓尔喀,边境才得以“安宁”。催促前进的圣旨如雪片般飞来。前线清军正在优柔寡断、摇摆不定、畏敌不前。一位绿营愣头青兵,在重庆总兵袁国璜面前却夸下海口,说有绝招可以直插廓军大帅行辕,一举摧毁敌营。夸海口之人正是豪爽勇猛的曾受。此时,他还是刚走出伙房的小兵蛋蛋,按说,一个军队怎么也轮不到一个小屁兵来进行战略思考啊,那些将军、参赞、总兵、提督、把总呢?都是空戴花翎,空吃军饷的吗?小小士兵,什么东西!敢口出狂言,小心身首两分。曾受敢夸海口,是对国家忠诚,朝廷的效忠,是有慧眼独具的虎气,而非个人安危,更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对此大言,多数官兵以为他在说梦话,袁国璜虽说将信将疑,也想试试。袁总兵一改平时威严的眼神,眼瞳骨碌地转动起来,心想,不成功死些士兵不足为惜,可一旦成功了呢,必功归于他。你又想想,一位将军的成功勋章是多少士兵的血肉铸成。袁国璜没有犹豫,随即便命曾受率领一排身手矫健的敢死队遵命行事。曾受按谋进行,连夜偷渡河道,潜入山林,绕道夜袭廓军营寨,他接连炸破廓军几座营寨、卡子,袁国璜随即率大军掩杀过去,为清军前进扫清了障碍。当曾受裹挟一身冰雪得胜归来,一副披甲挂满冰凌,眉毛胡须沾满雪花,让人望之凛然而叹服。
清军越过喜马拉雅山,经过几场殊死战斗,攻入廓尔喀境内,很快清军兵临廓尔喀首都阳布(今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廓尔喀称臣投降,许诺永不侵犯藏境。终于凑足了那把龙椅上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
曾受在这次战役中,有勇有谋,屡立战功,用血肉之躯换来了史料记载短短一行字:“曾受因参与征廓尔喀之役,拔充外委”。这十五个字的记载,对我来说是嫌短了、少了,略去了多少艰辛曲折的过程;对于曾受来说又显长了,其实他只需要一个“拔”字,作为绿营兵难能越级提“拔”、擢升重用,该知足了。外委是清代才有的一种委选的武官,相当于把总、千总级以下的八、九品武官职。曾受“拔”上这关键的一步台阶,从此踏上了通向高高在上的封疆大吏之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