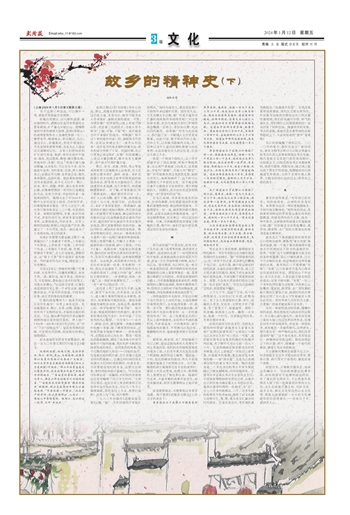杨永雄
(上接2024年1月5日第3期第三版)
关于这第三种说法,可以展开一笔,看能否更接近历史真相。
穿越历史烟云,注目春秋战国、秦汉唐明时代,武陵山区是丹汞资源的主要来源地,矿产量占半壁江山。楚辖黔地的丹汞资源得天独厚,涪陵(现郁山)的地理优势和水上交通优势独一无二,横贯东西,畅通南北,穿出郁江、乌江,通过长江,连通黄河,到达中原地区。丹汞是国家重要资源,也是乌江人遥远而又清晰的记忆。古先人们把块状的矿石进行筛选、粉碎,然后在炼炉中烧结、熔化,经过提炼、精炼、碳元素处理,形成朱砂、水银。经过一些道人僧人煽动欺骗,认为食后,可以长生不老,至少能延年益寿,当时皇家、官家、贵人争相食之;水银还可与铜、金形成合金,制作各种器具,包括兵器。据说秦始皇陵地宫用水银浇筑,至今无人打开。黔江、彭水、务川、武隆、酉阳、秀山有关史料记载,在隋唐时期这一带丹砂已是朝廷的贡品,官府主持汞、丹砂的开采一直延续到明代。隋朝大业十年(614年),黔中太守田宗显主持汞、丹砂的开采,向朝廷纳课水银达一百九十点五斤,其中务川每场炼汞达二三十挑,有获利近万者。清朝民国期间,水银、朱砂仍有开采,多是民间行为,官府多是设置事务所,从事收购汞、丹砂业务。历史上曾经因涪陵(现郁山)地区盛产丹汞,特建立了一个丹兴县,使这一地区成为了正史的伏线,史记的副本。
发现矿床需要火眼金睛。《管子·地理篇》曰:“上有赭者下有铁,上有磁石下有铜金,上有铅者下有银,上有丹砂下有金,上有陵石下有铅、锡、赤铜,上有银者下有铅”,古人目光如炬,慧眼识宝,这“管子六条”至今是探矿者的秘诀。丹砂富有的乌江大地,因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载:“巴寡妇清,先其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赀。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从这段文字看,巴寡妇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实业家,她因继承祖业,开采丹砂而致富,不仅有钱有势,而且受到秦始皇的尊重。
巴寡妇清是哪里人?她采丹的地区在什么地方?历史上未有定论。有说她是彭水、黔江、长寿、涪陵、武隆人,均有待于实物的证实,才能得出最后的定论。不过,她从事丹砂的开采运输和销售的地区是有据可查的。晋人徐广(352年—425年)在注《史记》时,在“丹穴”下注“涪陵出丹”。但此处所指的涪陵,不是现在的涪陵,而是现在的郁山周围地区。
彭水地域历史研究专家蔡盛炽,曾在一九九〇年第五期《四川地方志》载文:
汉朝的涪陵,地域辽阔,包括今彭水、黔江、酉阳、秀山、石柱南部、武隆东部以及贵州思南以北各县广大地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任乃强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中指出,“郁山不仅有盐泉足以聚民兴利,还是我国古代盛产水银与丹砂的地区。”“秦始皇时寡妇清,她好几辈人,都是以开采涪陵丹穴而连续致富。”“涪陵的采丹按货殖传‘擅其利数世’的推测,则应是战国初年便已兴盛起来的。”作者还进一步提出,“此区出产的丹砂,是以舟循郁江、入乌江……商运入中原销售的。故郁江、乌江的这一段河,又叫‘丹涪水’。”
如果以郁山(时为涪陵)为中心的话,那么,武隆东部的银厂村距郁山不过百里之遥,又邻乌江,极有可能为古人开采银矿,炼制水银的遗址。不然,为何在银厂坝背面的山坡上形成三级台阶,居住着三处居民点,当地人至今称为“上银、中银、下银”呢?或许就是当年开采银矿的地点。相距银厂坝不过十米的地方叫水厂坝,查阅现当代资料,这里从未建过水厂,地名从何而来?或许是当时炼水银时的蓄水池,取水的地方传承了下来。民国时期,在江口贾角山采过铁矿,在银厂村的落鹰山上采过大量的煤炭,煤中含有大量磷矿,这个地方可谓矿藏丰富。
黔江、彭水、武隆、酉阳、秀山等地采砂炼汞工艺被称为土法炼汞,其工艺流程主要为采矿、淘砂、炼汞。采矿在铁器工具未出现之前多用最原始的高温淬冷法,即先用大火猛烧岩石,然后迅速用冷水泼洒,岩石炸裂后,再沿缝隙凿取砂矿。有了锤、钎等铁器后,有了凿洞采砂,一般矿洞仅仅只容一人,采矿人以皮为帽,悬灯于额,洞深最远可达十五六里,经宿乃出。火药出现后,采矿才变得容易些。所谓淘砂,就是将砂矿捶打成细沙颗粒,然后放在摇船上的摇篼中用水淘洗,被过滤的浊水在船中沉淀,沉淀物就是混合着的丹砂矿砂,最后将矿砂在淘盆中多次反复用水筛选,即可直接得到红色的丹砂。淘出丹砂后,剩余的矿砂则用来炼汞。炼汞有特制的汞灶,汞灶由一条两米长的火道和一前一后两口厚重的铁锅组成,铁锅上放置竹甑子,竹甑子上再放一口底部有缺口的铁锅,缺口上倒放一个坛子(盎)。高温冶炼,当温度达到高度时,锅内的矿砂受热后蒸发的汞蒸气上升,在坛子内遇冷凝固,这种凝固物就是汞。古法炼汞,采用燃香计时法,即在灶的旁边插一炷香,当香燃到一半时,将坛子迅速取下,然后把附在坛子内壁的汞抹下,当地人叫抹“盎”,再将坛子放回原处。一炷香燃完,再抹一次“盎”,这一锅矿砂就算炼完了。一支灶一天一夜可以烧出汞一斤。
在历史上为了寻求长生不老,从秦汉、唐宋千余年间,许多皇帝、达官贵人、道人僧人等炼丹制汞从未断绝,连李白、杜甫都炼丹制汞而食。据说宋朝黄庭坚被贬彭水时,也炼过丹,他将郁山的一所学校题为“丹泉书院”。炼丹而食,绵延到明朝时仍然盛行,著名作家祝勇在《纸天堂》一书中写道:“万历皇帝的内心版图,一天天变小——由天下、朝廷、后宫、最后萎缩一具躲在帷幄中的瘦小身体,除了被窝里的快乐,只有炼丹能令他振作精神……拼命地炼丹,企图延长自己的生命。那是一股黑色的隐秘激情,调动了他身体中所有可能和不可能的能量,青红的炉火映照出皇帝焦虑的面孔。如同春药的热衷,他不可挽回地陷入悖论——闪烁的金丹,包含着对延时的许诺,但它是建立在预支时间的基础上,它通过对时间的预支来满足人们对时间的期待,而透支者,不仅要偿还他们的本金,还要付出利息,使时间的存款日益减少。可以说金丹的事业是一场骗局,对时间的贪婪使这位皇帝输掉了自己半生时间。”大家可以看出,这位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万历皇帝对金丹如此贪念,可以几十年不上朝理国政,那些皇臣士大夫、商贾巨富呢?自然上行下效,风行朝野。
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武隆县地名录》记载:“银厂,早年因境内开采银矿而得名。”询问当地老人,都说是祖辈口耳相传开采过银矿而来。因年代久远,又无史籍文字记载,银厂村是不是因为巴寡妇清炼制丹汞而得名呢?不过汞俗称水银,在古代炼制丹汞时,炉场四周会飘落一层粉尘,看似如白霜,发出闪闪的银光。如果银厂村名与此说成立,那凸显了这一方秘境人文历史更为厚重。由此可见,数千年的丹砂之地,丹砂之光,以其极为隐秘的文脉,有一份难以为外人道出的惆怅落寞与淡淡乡愁,永远存留在后人的记忆里,总是让人挥之不去。
我是一个执迷不悟的人,从小学开始就学会了胡乱猜题,明知不知晓答案,还认真严肃地画上勾或叉,这类做法,学生叫“猜题”,当地人叫“赌宝”。银厂村可能喜欢我这类胡思乱想、脑洞大开的人,如果妄测对了,这个村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文化。说不准会吸引来不少做地方文化史研究、考古和探秘的人。到那时,说不定村里还会给我颁发一本“荣誉村民证”呢。
在乌江流域,寻求某处地名的沿革,历史的渊源,往往需要调动所有想象的智慧和神经,做这种拼图游戏。不能期望在一时一地,就获取到最可靠的结果,必须永远做这种推测游戏。这个方法颇费周章,而又难以一时以定论的事情。后来,当我触摸那些深埋地下粗糙的石器、陶片时,他们开始向我呈现或证明历史深处的秘密。
四
那天造访银厂村委会时,村支书忙于去开会,落下孤零零的我,我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独自走进了一处叫蒋家坝的平地里,沿着新浇筑出来的水泥人行道,穿过一片红苕地和橙子树林,走向了乌江边。驻足眺望,乌江两岸,是一栋又一栋美丽的民居,两岸那些住所仍然在那陡陡的山坡上紧紧聚集在一起,笼罩着山峰那巨大的阴凉。村委会前宽阔的公路上,汽车轰轰隆隆地来来往往,稍隐绿荫的山腰间高速路、铁路车辆穿梭不停,但咫尺之间的村子依然寂静如常,浓荫掩映,四处弥漫着水果淡淡的香气。
我将远望的目光收回,开始注目脚下这片约有几十亩的平地,大地仿佛睁开漆黑的双目,永恒地注视着一切,始终一言不发。要打破这死寂般沉静,我偶尔将目光投向蒋家坝一左一右的黄草场和水厂坝。这三处都是亘古的江水从上游冲刷而来,含泥带沙形成的堆积坝,早年是连成一片的堆积层,如今因银盘电站蓄水,平坝靠乌江的边处,被翻腾的河水,卷曲成像美丽少女的裙边。
黄草场、蒋家坝、水厂坝皆铺展于乌江之畔,遥远迁徙而来的人类便在平坝上筑巢而居,他们的灰烬趁机混着泥沙成为土地,人们长年累月在此生活落下的遗物,被层层泥土掩埋。那连成一片的,低沉而凝实的波动,终久不衰地回荡在地表之下的黑暗之中。当石器、陶瓷的碎片凝视那无处不在的漆黑时,那泥土中生出梦境,恍惚之中,那黑暗的土地便生出了颜色和生命。随着时代走来,丰富有趣的故事开始发生,如今发掘出来,似有无数事物从土地中复苏。
读者需要铁证,不需要我过多卖弄风骚。我干脆将《武隆县文物志》上的文字抄录在下:
黄草遗址位于武隆江口镇黄草村黄草老街,属库区,海拔一百九十米至二百二十米,地处乌江左岸二级台阶地,遗址台地整体呈扇形,遗址前部为坡地,后部为国道,北有无名小溪汇入乌江,向南四百米为黄草渝怀铁路大桥。古遗址中后部为黄草场,地势平坦。遗址南北长约二百四十米,东西长一百四十米,占地面积约三万三千六百平方米。在遗址中部作地层分析,其文化堆积层分为五层,文化层厚度一百八十厘米。
蒋家坝遗址位于武隆江口镇银厂村一社,属银盘电站库区,海拔一百九十米至二百一十五米,地处乌江左岸二级台阶地,南北分别有一道冲沟,东至国道,西距乌江八十米,南至小麻园,北至沙丘,北隔大堰沟与水厂坝遗址相望。遗址分布在南北长二百米,东西宽一百米的范围内,面积约二万平方米。地层分六层,文化层厚度约二百三十厘米。
水厂坝遗址位于武隆江口镇银厂村六社,属库区,海拔一百九十米至二百二十米,地处乌江左岸二级台地,南北分布一道冲沟,分布范围南至大堰沟,北至无名冲沟,东至国道,西距乌江五十米,南隔大堰沟与蒋家坝遗址相望。分布在南北长二百米,东西宽九十米,面积约一万八千平方米。有文化层五层,厚度一百九十厘米。
三处古遗址和盐嘴店遗址出土有石制品多件,分别为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砾石端刃石器、石片石器,有石锛、石斧;还有更多的含泥质素面陶片、夹砂绳纹陶片、矢状燧石质雕刻器、陶盏、陶缸残片等。
考古追寻人类的智慧,器物留存文明的脚步。考古专家初认定为新石器至商周时代文化特征。银厂村那厚重的泥土,任一抔有千钧之重,狂风将它们飘扬于乌江间。这些石器、陶片经过漫长时间的征途,永远在这里沉默不语,地上之人受此感召而震动,地底下的生命从黑暗中显现出来,不再安眠于我宽厚的故乡。我想,不会有人再说我们所处之地是一处古老的“蛮荒”。否定乌江流域的文明史,则是荒诞不稽的。
上下几千年,迢遥千万里,风干的筋骨犹在,尘封的记忆不泯,有物为证。有了古人类遗留的石器、碎片,武隆的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才有了颜色,有了葱茏万千,绿意盎然。借你一色斑斓,染我故土山水。蘸你一点灰色,绘就一个时代。历史能证明历史,未来在期待未来。
在我沉浸在写作此文时,全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武隆考古又有重大发现!”近期在距黄草场十公里的江口镇乌江北岸出土的“关口西汉一号墓”,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有明确纪年的最早西汉墓,其下葬年代为公元前一百八十六年。它是西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木椁墓,长江上游地区一次性出土漆木器、竹器最多的墓葬,重庆地区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清水墓”,也是乌江流域秦汉时代的重大考古发现。吸引全国各地二十多位顶尖的考古专家齐聚武隆江口镇发掘现场,共同发掘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从墓中出土的告地书确定墓主人为西汉官员,是西汉惠帝时期的一位御史,名“昌”。出土六百多件随葬品,二千二百多年前的板栗至今色泽油润,展现了汉文化确立进程中巴、蜀、楚、秦文化交汇融合的时代特征。记者在采访中,考古领队黄伟教授说:“纯属意外发现”。在我没来黄草场两周前,我约区文联主席刘民、作协秘书长杨武均曾到过关口西汉墓发掘现场,我们好奇地问年轻、帅气的黄队长,你们用什么仪器探测到的?他也回答了同样的话。随着科学的发展,考古的进程,谁能否定在黄草场附近暗黑的泥土下,不会有惊奇的“意外”发现呢!
乌江的风唤醒了我的记忆。二〇一〇年的夏天,我时任县文广新局局长,重庆文物考古所白九江院长带着大批考古队员正在蒋家坝遗址考古发掘,我代表地方文化部门前往现场慰问。在验收会上,白院长陈述考古发掘成果时,我两耳震响、两眼发亮,随之闭上眼沉浸于那光芒的怀抱,仿佛暗淡的白昼被虚无所照亮,太阳于水面中落入世界,万物又回到久远的过去,那存在之前的故乡。
五
著名作家阿来说:“村有自己的历史。村的地质史。山神的化身为历史。如果要为这后一种历史勉强命名,不妨叫地方精神史。”按阿来的说法,我将黄草场附近的罗家堡从漫长传承的儒释道,到接受西方的天主教,视为一种开放史,这种独有的地域文化是秘境之秘;银厂村的地名文化和盐嘴店、黄草场、蒋家坝、水厂坝的古聚落址的探寻是地方精神史。
地处乌江下游武隆东部的黄草到江口的峡谷地带,媒体用“重大发现”来表述惊喜,是一个基于黄河流域或中原地方对西南地区不恰当的道德评价。显然,“发现”这个词里暗藏着主流文化的某种优越感,而江口镇的黄草,以它不可言喻的完美,恰好构成对这种优越感的反讽。黄草到江口不需要被“发现”,“发现”江口的黄草不是乌江的幸运而是我们的幸运。那里的山千年还在,水万古长流,人类在蓝天碧水间茁壮成长,从来不曾中断。“发现”一处二千多年的西汉墓不必惊喜,早些年已从盐嘴店、蒋家坝、黄草场、水厂坝发掘的新石器的石器加工场,商周时代的古聚落址证明了在八至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居住。那些传承几百年的天主教,古老银厂的地名就显得不足为奇。
任何一种曾经清洁的宗教,随着时间的流逝,都在世俗化与政治化的过程中,令人痛心地礼崩乐坏。地名往往烙上某处大地上的过往和自然形态,在漫长历史中存在或消失,存在是一种固化史,消失被另一名称所替代,这种消失、替代是历史一种严格的法则,我们苦苦追寻的“银厂”这个地名来历,其实是追忆一种精神流传的过程。那些深埋泥土下的石器、碎片,暗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就是人类走来的轨迹。
天主教被风裹挟在摇摆不定之中,村名暗隐于无尽岁月混沌的世界里,那些石器、碎片毁灭于漆黑的、暴乱的某个夜晚。
回望历史,云雾散尽清风在,惊涛过后巉岩兀。空间距离最近的黄草场,却给我留有可追溯的遥远时间。有了漫长的文明岁月,才让我意外获得古人留下的一份厚重而珍贵的大礼包,这礼包装着石器文化、丹砂文化、地名文化、教义文化和自然山水文化等,那是大地遗留给一方人的文化渊源和自信的贵重礼——恢宏五千年,温润世人心。